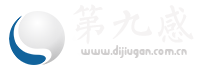在健身房遇到了学哲学和心理学的健身教练 | 心藥篇
来源: 作者: 发布日期:2022-02-17 访问次数:387
倏然间,时间迈入了2021的年末。在体检报告出来前的一晚,我度过了同样不安的时间,但也是在这辗转反侧间,我想到: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,人,无论如何,终究是会走向衰败。于是便没有再焦虑,坦然睡去。两周后,体检报告出来了。报告显示,各项指标仍保持在正常区间。
我知道,健康指标终有一天会掉头朝下,但只看当下的话,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,不进不退也欢喜。这一年多来,我逐渐养成了规律运动的习惯,着规律本身也给我带来欢喜,更何况,还有我欢喜的教练,和他带给我的全新世界。
我的健身教练,
有心理学与哲学背景
我称教练我的为“师父”。师父和我同龄,本科心理学,硕士读哲学。闺蜜小慧慧说,就冲这学科背景,也值得心动。
一次,我偶然和师父提到最近在看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,后来他问我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里喜欢哪个人物。当时我便愣住了,因为那本书看了一半被我撂下了。那种感觉,就像自己是个存有侥幸心理没有完成作业的高中生,偏巧被老师查到,好不紧张,磕磕巴巴说了个胡塞尔就落荒而逃,生怕露馅被看出端倪。
细想起来,书里的人物,梅洛庞蒂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。他是全书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散发温柔光芒的快乐哲人,就像给我上课时的师父。但是,师父也仅在我的私教课时间内是梅洛庞蒂。在别人的私教课时间,他之于我就是虚无。现实生活中的他更像书里的萨特——一个为了自己选择的事业不知疲倦付出的人。
梅洛庞蒂温和优雅,讲究与世界达成妥协,以此确立个体的存在。萨特热烈激进,一直在奋斗、抗争,以此获取个体的自由。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。而现实中,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有他们俩的影子。
因为健身的巨大收获,我对师父感恩戴德,以前每季度会写长长的信给他。里面讲的初心是,我不要像父亲一样,在生命最后的十年虚弱绝望,一点点耗干能量。后续又开玩笑般地写,我不要在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,只能呼天抢地,我要具备背起他们就跑的身体素质。
某天,我在“中国器官捐献”公众号上登记,成为了一名捐赠志愿者。干了这么大一个事,必须要发圈呀。没想到,一个朋友看了,自己也马上登记成为志愿者了,说从此以后也不能随意挥霍身体了,怕到时候用不上。回头,我骄傲地给师父发微信:“咱好好练,到时候捐遗体,得让医学院的小崽子们对我翘大拇指才行!”
睡觉也要继续锻炼
某次,我在手机上看到小一个视频:两个姑娘打擂台做引体向上,都一口气可以做上十几个。看得我好不羡慕。我也要去做引体!说干就干,转眼间我就到了健身房,双眼死死地盯住上方的杆子,手握紧,收核心,沉下肩胛骨往里收……
“嗯”一声丹田用力——我醒了。原来是在美容院做护理睡着了,不禁哑然失笑。
在梦里锻炼这件事其实经常发生,我不止一次梦到过自己正在做高位下拉,划船机……还有一次梦见师父为了锻炼我的心肺,整一只我最怕的臭大姐把我追得满场跑。师父管这叫“精神锻炼”。
引体向上,师父曾为此对我大加赞赏,说我是他女学员里头一个自己能拉引体的。但之前我都是使用的对握握杠杆,后来换成正握后,顶多能自己起一个,再来,眼睛到杠的位置,就上不去了。这个途中,那种难以控制的挫败感,是最让人心生恐惧的。
拉完引体向上,师父会说,看你明天后背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疼。他经常这样说,因为确实经常意想不到。今天最疼的地方是肩膀的前下方和后下方(肩胛骨外侧),肩胛骨内侧也有感觉,但是不严重。
经过引体,我发觉:自己的身体竟像是黑箱一样扑朔迷离。之前做卧推的时候,师父一直在强调夹胸,而我即使做到崩溃也推不了几把空杆。结果第二天,胸不疼,胳膊疼,意不意外?惊不惊喜?
其实,每一个个体本身也是一个黑箱,就像当年没人能解释:不运动不肥胖也无不良嗜好的我,单纯肌酸超高,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事实上,人不是全知全能的神,各种理论自然都有局限性,对付身体这个黑箱,也是面对人不全知全能这一现实的智慧吧?而我,作为身体黑箱的主人,也别无选择,只能保持信任,坚持日常训练,偶尔难得糊涂。
儿子,我的第一个健友
大科是我的儿子,也是我在健身房的同学。作为第一个被我介绍进健身房的健友,我不太想提起他,更不喜欢讲他与我的关系。作为母亲,我从骨子里全心全意地爱他,正因为如此爱他,我一直刻意保持与他的距离。我想让他尽可能少地受我的影响,尽可能多地吸收各处的营养,“成为千百万人而始终保持他自己。”当他再大一些,在此后的一生中,不必背负原生家庭、严厉母亲的沉重心理负担,而能够从滋养过他的家庭中汲取力量,自由发展自己、成就自己。
我给大科报的兴趣班不多,因为大多数兴趣班的老师只是在教一种特定的学问或者技巧,这种东西我颇看不上眼,就像妈妈天生看不上孩子吃方便面一样。现在大科在上的课外班,一个是攀岩,一个是作文,一个是跟着师父在健身房训练。作文班的老师是我暗中观察多年的一位良知满分,学识八十分的老师。我没盼望孩子可以从几节线上作文课中获得什么分数上的提高,但是老师会在班上讲福克纳,讲聚斯金德,这就相当了不起了。
大科最开始攀岩的时候,上去的还算顺利,但是他不敢下来。他那时在十米高的岩壁上嚎啕大哭,就是不肯松开手脚。一个大块头的八九岁的男孩子,哭声在高大的岩馆里十分响亮,让孩子的父母颇为脸红。
不过后来,大科便走上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攀岩之路。今年夏天,我去为他的一次攀岩比赛加油助威,这才发现,我家那个曾经在岩壁上嗷嗷哭的娃娃,经过一年多的训练,完全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在岩壁上闪转腾挪,不断做出“反提”、“反肩”、“飞”这样的技术动作。这些名词我并不太懂,但是我看到了他周身都散发着自信与力量的光芒。
更让我感触的是,当比赛中排队上一条线的时候,我对他说,“你快看看别人是怎么爬的,自己心里过一遍。”他用专家一样的口气对我说,“不用看,每个人的力量水平不一样,同一条线路上每个人的发力走线都不会相同的。”然后继续语气平静,“这条线我爬不上去。”
平日里写作文或者遇到不会的数学题,大科会撒娇一样地扭着身子,跺着脚,愁眉苦脸,哼哼唧唧。而在岩馆,他具有了一种能平和看待困难,承认不足的可贵心态。大科的这一句话,让我心服口服,我知道,他已经在岩馆学到了更重要的东西。
不过攀岩也讲究天赋,我在岩馆里看见那些身手矫捷的人,一般都是手长脚长,干干瘦瘦的。我们大科可不是这种体型,他长得虎头虎脑,颇为壮实。十岁的年纪,手腕已经比我的还要粗不少了。所以他在一起攀岩的小伙伴里,成绩是倒数的。
我因为自己从健身房受益良多,想到可以“润物细无声”地助他一臂之力——给他买私教课,健身课上的发力技巧,也许会对他的攀岩有所裨益。听上去奢侈,但是对比动辄一小时六七百的学科辅导,这种看似最无用其实最有长远效果的体育一对一,我觉得简直是超值。
于是,大科在我拜师半年多后,也被我领进了健身房。现在,他经常会盼着我可以和他一起训练,于是,我就变成了健身房外间等着被“叫号”的“路人甲”:穿一身运动服,一边读书,一边等师父喊我进去,给大科当陪练。当陪练还要适当地示示弱装装傻,以保护小朋友的兴趣。
平日里,大科一周上一次私教课。我并不问他课上练了什么,但是上过攀岩课,大科会眼睛亮晶晶地说,“健身老师教我的发力方法很有用,我今天突破了一条V3线路!”
我知道,健康指标终有一天会掉头朝下,但只看当下的话,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,不进不退也欢喜。这一年多来,我逐渐养成了规律运动的习惯,着规律本身也给我带来欢喜,更何况,还有我欢喜的教练,和他带给我的全新世界。
我的健身教练,
有心理学与哲学背景
我称教练我的为“师父”。师父和我同龄,本科心理学,硕士读哲学。闺蜜小慧慧说,就冲这学科背景,也值得心动。
一次,我偶然和师父提到最近在看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,后来他问我《存在主义咖啡馆》里喜欢哪个人物。当时我便愣住了,因为那本书看了一半被我撂下了。那种感觉,就像自己是个存有侥幸心理没有完成作业的高中生,偏巧被老师查到,好不紧张,磕磕巴巴说了个胡塞尔就落荒而逃,生怕露馅被看出端倪。
细想起来,书里的人物,梅洛庞蒂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。他是全书中唯一一个自始至终都散发温柔光芒的快乐哲人,就像给我上课时的师父。但是,师父也仅在我的私教课时间内是梅洛庞蒂。在别人的私教课时间,他之于我就是虚无。现实生活中的他更像书里的萨特——一个为了自己选择的事业不知疲倦付出的人。
梅洛庞蒂温和优雅,讲究与世界达成妥协,以此确立个体的存在。萨特热烈激进,一直在奋斗、抗争,以此获取个体的自由。两个人最终分道扬镳。而现实中,我们每个人都同时有他们俩的影子。
因为健身的巨大收获,我对师父感恩戴德,以前每季度会写长长的信给他。里面讲的初心是,我不要像父亲一样,在生命最后的十年虚弱绝望,一点点耗干能量。后续又开玩笑般地写,我不要在家人需要帮助的时候,只能呼天抢地,我要具备背起他们就跑的身体素质。
某天,我在“中国器官捐献”公众号上登记,成为了一名捐赠志愿者。干了这么大一个事,必须要发圈呀。没想到,一个朋友看了,自己也马上登记成为志愿者了,说从此以后也不能随意挥霍身体了,怕到时候用不上。回头,我骄傲地给师父发微信:“咱好好练,到时候捐遗体,得让医学院的小崽子们对我翘大拇指才行!”
睡觉也要继续锻炼
某次,我在手机上看到小一个视频:两个姑娘打擂台做引体向上,都一口气可以做上十几个。看得我好不羡慕。我也要去做引体!说干就干,转眼间我就到了健身房,双眼死死地盯住上方的杆子,手握紧,收核心,沉下肩胛骨往里收……
“嗯”一声丹田用力——我醒了。原来是在美容院做护理睡着了,不禁哑然失笑。
在梦里锻炼这件事其实经常发生,我不止一次梦到过自己正在做高位下拉,划船机……还有一次梦见师父为了锻炼我的心肺,整一只我最怕的臭大姐把我追得满场跑。师父管这叫“精神锻炼”。
引体向上,师父曾为此对我大加赞赏,说我是他女学员里头一个自己能拉引体的。但之前我都是使用的对握握杠杆,后来换成正握后,顶多能自己起一个,再来,眼睛到杠的位置,就上不去了。这个途中,那种难以控制的挫败感,是最让人心生恐惧的。
拉完引体向上,师父会说,看你明天后背会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地方疼。他经常这样说,因为确实经常意想不到。今天最疼的地方是肩膀的前下方和后下方(肩胛骨外侧),肩胛骨内侧也有感觉,但是不严重。
经过引体,我发觉:自己的身体竟像是黑箱一样扑朔迷离。之前做卧推的时候,师父一直在强调夹胸,而我即使做到崩溃也推不了几把空杆。结果第二天,胸不疼,胳膊疼,意不意外?惊不惊喜?
其实,每一个个体本身也是一个黑箱,就像当年没人能解释:不运动不肥胖也无不良嗜好的我,单纯肌酸超高,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事实上,人不是全知全能的神,各种理论自然都有局限性,对付身体这个黑箱,也是面对人不全知全能这一现实的智慧吧?而我,作为身体黑箱的主人,也别无选择,只能保持信任,坚持日常训练,偶尔难得糊涂。
儿子,我的第一个健友
大科是我的儿子,也是我在健身房的同学。作为第一个被我介绍进健身房的健友,我不太想提起他,更不喜欢讲他与我的关系。作为母亲,我从骨子里全心全意地爱他,正因为如此爱他,我一直刻意保持与他的距离。我想让他尽可能少地受我的影响,尽可能多地吸收各处的营养,“成为千百万人而始终保持他自己。”当他再大一些,在此后的一生中,不必背负原生家庭、严厉母亲的沉重心理负担,而能够从滋养过他的家庭中汲取力量,自由发展自己、成就自己。
我给大科报的兴趣班不多,因为大多数兴趣班的老师只是在教一种特定的学问或者技巧,这种东西我颇看不上眼,就像妈妈天生看不上孩子吃方便面一样。现在大科在上的课外班,一个是攀岩,一个是作文,一个是跟着师父在健身房训练。作文班的老师是我暗中观察多年的一位良知满分,学识八十分的老师。我没盼望孩子可以从几节线上作文课中获得什么分数上的提高,但是老师会在班上讲福克纳,讲聚斯金德,这就相当了不起了。
大科最开始攀岩的时候,上去的还算顺利,但是他不敢下来。他那时在十米高的岩壁上嚎啕大哭,就是不肯松开手脚。一个大块头的八九岁的男孩子,哭声在高大的岩馆里十分响亮,让孩子的父母颇为脸红。
不过后来,大科便走上了一发不可收拾的攀岩之路。今年夏天,我去为他的一次攀岩比赛加油助威,这才发现,我家那个曾经在岩壁上嗷嗷哭的娃娃,经过一年多的训练,完全像换了一个人。他在岩壁上闪转腾挪,不断做出“反提”、“反肩”、“飞”这样的技术动作。这些名词我并不太懂,但是我看到了他周身都散发着自信与力量的光芒。
更让我感触的是,当比赛中排队上一条线的时候,我对他说,“你快看看别人是怎么爬的,自己心里过一遍。”他用专家一样的口气对我说,“不用看,每个人的力量水平不一样,同一条线路上每个人的发力走线都不会相同的。”然后继续语气平静,“这条线我爬不上去。”
平日里写作文或者遇到不会的数学题,大科会撒娇一样地扭着身子,跺着脚,愁眉苦脸,哼哼唧唧。而在岩馆,他具有了一种能平和看待困难,承认不足的可贵心态。大科的这一句话,让我心服口服,我知道,他已经在岩馆学到了更重要的东西。
不过攀岩也讲究天赋,我在岩馆里看见那些身手矫捷的人,一般都是手长脚长,干干瘦瘦的。我们大科可不是这种体型,他长得虎头虎脑,颇为壮实。十岁的年纪,手腕已经比我的还要粗不少了。所以他在一起攀岩的小伙伴里,成绩是倒数的。
我因为自己从健身房受益良多,想到可以“润物细无声”地助他一臂之力——给他买私教课,健身课上的发力技巧,也许会对他的攀岩有所裨益。听上去奢侈,但是对比动辄一小时六七百的学科辅导,这种看似最无用其实最有长远效果的体育一对一,我觉得简直是超值。
于是,大科在我拜师半年多后,也被我领进了健身房。现在,他经常会盼着我可以和他一起训练,于是,我就变成了健身房外间等着被“叫号”的“路人甲”:穿一身运动服,一边读书,一边等师父喊我进去,给大科当陪练。当陪练还要适当地示示弱装装傻,以保护小朋友的兴趣。
平日里,大科一周上一次私教课。我并不问他课上练了什么,但是上过攀岩课,大科会眼睛亮晶晶地说,“健身老师教我的发力方法很有用,我今天突破了一条V3线路!”
在师父和大科的鼓励下,我也在今年夏天尝试了攀岩。十米高的岩壁,上去容易,下来的时候,确实也犹豫了几分钟:这么高,这个绳子,扣好了吗?一番挣扎后,一咬牙一闭眼,松开了手脚,我的身子,像坐电梯一样缓缓降到了地面。

上一新闻:失眠抑郁的特征
下一新闻:谷爱凌展现超强“大心脏”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