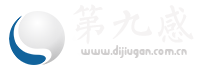气味, 还有声音
气味难写,因为抽象。有些天生的文字能手能把气味写到令我仿佛置身那种气味之中,令我由衷羡慕,甚至嫉妒。文中有句“念及伦敦,就记起地毯上灰尘的甜味”,瞬间把我带回旧友在巴黎的工作室。旅伴比我嗅觉发达,从巴黎回来后,一直对这种“地毯上灰尘的甜味”念念不忘。我们一起怀念这种味道的时候总词穷,想不到洪爱珠信手拈来“灰尘”和“甜味”两个字眼放在一起,就还原了我们念兹在兹的那种味道。
洪爱珠一定也是个鼻子灵敏的人,否则不会写下这样一段文字:“泰式料理中,香气是光影。很多时候你不真的吃着它,而是被它的投影所包围。香料们时而隐约幽微,时而飞扬明亮。在冬阴汤里,在咖喱酱中,在鱼饼里,在日子里。”最后四字可圈可点,寻常但又奇异,整个意境旋即荡漾开来,足见洪爱珠的文字功力以及魅力。你看看她如何描绘香茅的气味:“香茅气息比起柠檬的鲜爽,要木一些,拙钝而温和……”麻疯柑叶的香则是:“有些香气是朦胧的,团块似的,雾的。但疯柑叶不是。它近似柠檬的香气,清晰而尖细,是料理中的高音,颜色里最锐的青绿。”
我们通常弃之的芫荽根,在洪爱珠眼里是“泰国人的神奇宝贝,埋伏在众多菜色中,有时被捣碎得不成形状,或和其他香料混合,是料理人公开的密码。它仿佛丛林的、带湿气及泥土气息的异香,自己声量饱满,与他人合音亦谐。”以抽象的声音写抽象的气味,仿佛负负得正,效果具体生动。另一篇《钵与杵》,我以为是她对泰国的听觉上的怀念,结果不是,这篇文章是洪爱珠对钵杵这种古老工具的礼赞,以她跟泰国友人树小姐和树小姐远嫁英国的二阿姨Sao的交情贯串起来。
留学英国时期,她从Sao阿姨那里学晓食物调理机速捷但缺乏过程,有些食材就是需要时间处理,需要钵杵慢慢舂捣,才会产生绝佳的口感和香气,那不但是一种感官享受,手腕起落节奏固定,也可以是一种静心冥想。文中提及泰国人有一种择偶方式,就是听一个人操使钵杵,借由节奏急缓柔烈推测对方性格,多么浪漫。又写约旦瓦地伦沙漠中的贝都因人舂捣咖啡豆,金属磨杵发出声响,恰好告知四邻此有咖啡,欢迎前来享用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看这种庶民风俗图绘。